这个寒冬对于外卖骑手来说格外难熬:他们要么跑单在路上,要么就是阳了
#这个寒冬对骑手来说格外难熬#这个冬天对外地骑手来说特别难熬——他们要么跑单在路上,送完这一单,下一单就加班;还是“阳”在家,发高烧对着订单叹气。每躺一天就意味着损失一两千块钱。随着春节的临近,他们中的一些人今年特别想回家。
闻喜南溪
编辑×悉尼·金
在这个越来越多人“阳光”的冬天,外卖骑手成了北京最忙的人。骑手刘桐从早上8点到晚上10点出门,忙得连吃饭上厕所都顾不上。每天的订单量是之前的3倍多。
12月的外卖订单有了新常态——有的单子上写着“放在你家门口,不要打电话”;有顾客开门,戴着两个口罩,说是阳了,“远离”;有的门,只小心翼翼地伸出一只戴着塑料手套的手,取出后马上关门。有的人可能在家时间太长,或者不耐烦,开门上前,想和刘彤说话。刘彤下意识地往后退,说电梯到了,先跑一步表示尊重。
送有风险,取也有讲究。一个顺丰同城的骑手记得有个客人把要送的包挂在门把手上,酒精消毒的味道还留在上面。接受订单需要提货代码。他敲门,客户通过防盗门报出里面的号码。他看了看包。那是一盒连花清瘟胶囊。药品,是他最近送的最多的物品。
“爆炸令”
最近每天打开跑单App,刘彤都会发现,在线的同事越来越少了。12月13日,他的网站上只剩下12个人在运行订单,而前一天有19个人。这家位于通州物资学院附近的外卖骑手站点虽然不大,但也有三四十人的规模。夏天旺季能达到五十人,现在是他脑子里人最少的时候。
12月之前,街上有很多像他一样穿着黄色或蓝色棉袄的骑手,骑着电动车,四处奔波。偶尔下午的时候,我们聚在河边或者路边,在毛驴上休息,聊天,刷手机。但现在,原本拥挤的马路宽了好几倍,很少有车经过,方圆几公里内甚至找不到一个骑手。
“很多人年纪小,跑不动,就待在家里。还有人因为太冷,提前回老家了。”刘彤说。与骑手短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外卖订单激增。疫情政策放开后,越来越多的人被感染。在家自愈的人,需要靠外卖来“续命”。
在外卖平台上,通常半小时内可上的外卖时间调整为50到60分钟。有人点了一份酸菜鱼饭,饿着肚子等了一个半小时,被迫取消。最后,他们不得不翻冰箱,在饺子里煮。下午3点有人点了一份鸭脖,晚上11点半送到。其他人早上9点就开始订午餐。午饭后,他们打开手机点餐。虽然他们每次收到的食物都是凉的,但他们已经很满足了。
前两天,家住朝阳门地区的孙女士等了几个小时也叫不到顺风车,干脆去餐厅取餐。酒店门口放着几十袋打包的外卖,只有几个外卖员来取餐。“所有来接饭的人都跑过来,一边跑一边给客人打电话道歉”。
孙女士去餐厅取餐时已是晚上,累计订单基本都是中午。
十二月中旬,北京连续几天大风天气,局地阵风高达六到七级,全天气温在0℃以下,夜间低至零下十几度。从早到晚跑的骑手担心感染,还要小心大风低温。
一件厚底毛棉袄,保暖裤,皮裤,一顶帽子,一副皮手套,都是刘彤的装备。不要把衣服裹得太厚,因为跑步的时候总会出汗。驴子起步时,风像刀子一样吹在脸上,面具周围的颧骨和眼睛冻得发紫。
从上午11点到12点,刘通马不停蹄地跑了8单。他跑队单,基本距离在三公里以内。最近每天早上10点到晚上9点能跑50到80张票,最忙的时候都没空上厕所——如果路边没有公厕,我只能憋着不敢喝水。
过去,我们必须等待命令。有时候要等一两个小时才能拿到一单,中午可以休息一个小时左右。但现在,他要到下午两点才能吃午饭——在空荡荡的美食城点了一份12元的小吃,随意拖出来,坐了十几分钟,喝水抽根烟,然后继续赶路。
"基本上,你一放下东西,就会马上开始下一个订单."在刘通的App上,一个订单总是被下一个推出来。送完这个订单,下一个订单就超时了。
晚上六点,刘通的两单都是加班。附近一家麦当劳的常驻骑手工资拿了一大半,人手不够,就被调去帮忙了。麦当劳的两个订单发给他的时候,只需要几分钟就会超时,而且还是两个方向,不管怎么发都会超时。虽然最近平台不处罚加班单,但刘彤看到不断有新单进来,心理压力很大。
订单收到后,只剩几分钟就超时了。
商家也断单了。有的店地上放着很多现成的外卖食品,也没人送。与此同时,机器上的订单不断弹出。一家刚刚开业,专门做外卖的油炸酸奶店,每天都在赔钱——因为附近没有骑手接单,每天都有近十单送不出去。商店不得不调整策略,等待骑手接单。
有订单堆在一个店铺里,却没有骑手来取,订单就断了。
除了外卖,最近骑手送的最多的是药。同城的一位顺丰骑手表示,上个月,他的订单中超过一半是送药。“可能是因为快递送不到货或者到不了。有的亲朋好友会互相送。”根据闪付平台数据,12月1日-12日,北京用户医疗订单较11月同期增长2194.6%。
在运力不足的情况下,政府机构也开始积极调配人力资源。12月16日,海淀区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发布《关于参与外卖配送服务的倡议》称,受疫情影响,部分外卖企业不同程度削弱了运力,订单配送压力大,呼吁已接种三枪、有电动车的“阴性”居民成为骑手。
骑手阳
就在刘通疯狂接单的同时,外卖骑手王兴发现自己在离通州40多公里的昌平北齐家村。他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被感染的。12月8日上午,他跑了天通苑、北七家、回龙观。在路上骑车时,他感到发烧和头晕。他回家量体温,正在发烧。他赶紧去药店买了抗原检测,呈阳性。
虽然之前也有过各种关于“阳”的新闻,但是对于很多车友来说,感染还是很突然的。王兴家里没有任何毒品。药店里的布洛芬和连花清瘟胶囊已经卖完了。不想空手回家,他买了一些不对症的药。他向村委会举报,对方让他回家休息,把他当感冒看待。
还好住在附近的哥哥送来了一盒连花清瘟胶囊,抗病毒感冒颗粒,一袋水果。他把一个好心人的礼物拍了下来,发了朋友圈,抖着嗓子,配上“谢谢你雪中送炭,等我准备好了,我就来感谢你”的文字。一个来自甘肃的骑手,一周前也是阳了——发烧近40度。他先是冷,然后全身发烫,眼睛红红的,眼睛火辣辣的疼。他的外包团队有五六十人,一半都被感染了。大家每天都在群里举报。
感染前两天,王兴几乎所有时间都躺在床上。他的症状很明显,发烧,声音嘶哑,身体虚弱。随之而来的是压力和内疚发泄季,时间就是金钱。王兴是众包,不追求单量,而是总里程。他的电动摩托车以每小时50英里的速度行驶。他一般早上7点出门,一直跑到晚上12点。最多的时候,他一天跑六七百公里。
现在每躺一天就意味着损失一两千块钱。
他所在的小组里的外卖骑手,最近除了感染,说的最多的就是最新的单量和收入。现在跑团每单能达到7.5元,众包订单的数量也是层出不穷。大家都在城市里跑来跑去,想多赚点钱回家过年。
这个冬天对每个车友来说都很难熬——从11月底开始,北京很多小区进入封闭管控期,只能进出。有的骑手被关在家里,有的干了一天发现回不了家,有的开始在外面流浪,比如王兴。
担心自己被堵在小区里接不到单,就骑电动车带着被褥和行李在外面游荡,住在公园里,睡在立交桥下。清晨路边的空地上,一张铺着粉色被子的便携式长沙发就是他的床。他也找过空无一人的商场,睡在楼梯间。最后买了个帐篷,在公园的空地搭起了帐篷。冬天北京气温零下十几度,土地冷得像钢板。他用送饭时的保温袋垫在身下,裹在睡袋里,听着疯狂呼啸的北风,凑合了一夜,等待天亮。
王兴曾经在外流浪十天,用短视频记录生活。
群里很多骑友都在分享“流浪生活”——有人说跑累了就睡在摩托车上,睡不着就继续跑。有人在森林公园的长椅上住了差不多一个星期,或者呆在地下车库里。其他人住在学校对面的公共厕所里。虽然很臭,但至少很温暖。更多的人住在桥洞里,脚被冻死。
“每个月都要交房租,还要拿钱养家。在外面,我至少可以继续工作。”一位骑手说,他们宁愿在外面跑,也不愿在被窝里无所事事。那段时间订单猛增,大量生鲜超市订单涌入。高峰期超市断单,一下子出来两三百单,前面几百单被卡住。有些小超市自己老板忙,根本接不到货。
即使涨价,也未必有人接单。有车友记得最高加价甚至高达100元,超过了商品本身的价值。“太重了。”王兴说,有一次他把十几斤的货物放在后座,路面不平,车一颠簸,车架就断了。那天拉了几单,赚的钱都用来修车了。
在流浪过程中,电动车不仅载着外卖,还载着自己的行李。
今年我想回家。晚上九点,北京通州,七级大风把刘通的电动车刮倒了,车把手也断了。他本来要加班到晚上10点半,现在只能回家了。
“外卖行业,很少有人真的愿意做,但是没有办法。门槛低。如果会骑电动车,会用手机,就可以完成了。没有学位不需要文凭。”刘桐是河北承德人,女儿在老家。每月工资很大一部分寄回给女儿作为生活费,自己只留一些必要的开销。冬天刺骨的北风让他为苦难而哭泣。很多车友会在最冷的时候离开,春天过后再回来。
低温天气是车友们最大的担忧之一。
王兴对此也习以为常。跑了这么多年,很多以前的熟人都不见了,有的人回老家创业,有的人挣钱做其他工作。但也有新人加入进来——生意失败的老板,打牌输了的赌徒,出来吃外卖赚快钱还债。王兴在北京卖食品已经快十年了。他喜欢跑5公里外的单子。他的工作虽然繁重,但收入是在家乡种地的很多倍。
“一进门就是卧室,然后是厨房,紧挨着厕所。每月租金1200元。”他这样介绍自己在北京的家。“家”在昌平北七家的一栋公寓楼里。除了一张小桌子、床和电视,卧室里最引人注目的是墙壁——一张淡黄色的塑料壁纸,上面有吉他、两个小人和墙砖的图案,还有一个摩托车牌照。
王兴平时早出晚归,家只是一个落脚点。送餐的时候总会出现各种情况。有时候他到了小区门口,门禁坏了,客户过不去,要在寒风中等十几分钟。有时候我在楼下打电话,客户说洗完澡就拿,不知道要等多久。
还有一些好心人,看着他送食物,送一瓶水,送一点巧克力,会记住他很久。这三年,他学会了一些自我保护的措施——戴N95口罩,送上门,敲三下门,叫客户来取,不联系就送。
最让王兴津津乐道的是他在送外卖的路上救人。一天晚上他进一个小区送餐,骑车到一个偏僻的角落,看到一辆黑色的路虎。车门开着,钥匙在车里,人躺在路中间,有酒味。他们中的大多数都醉得动不了了。他叫来保安,打了110,一直等到警察来了才安全离开。还有一次,他去重灾区运送防疫物资。途中,他遇到一辆电动车被公交车撞倒,骑车人血流了一地。他还帮过警察,然后订单就是加班。
半夜一两点钟,他常常忙完一天的跑单回到家,吃点夜宵——一碗白米饭堆了七八根辣条,一个不锈钢盆里装了火腿肠和豆腐干,一小杯里倒了一点酒。面对贴着壁纸的墙壁,他用手机录制视频。“生活中能交心的人不多。做好自己,善待自己。”
他最后一次给四川老家打电话,他妈妈劝他回去过年。他一脸不情愿,说今年没赚到钱。三年来,因为买不到票,封城,他没有回家过年。老婆跟他离婚了,女儿9岁。她是在老家被爷爷奶奶带大的。他说女儿对他越来越陌生了。每次打电话,他爷爷奶奶都会替她说几句话。
王兴心疼女儿,但他没有办法。想到老家的几间土房、年迈的父母和女儿,他只能继续在偌大的北京城里奔波。太阳落山后的第七天深夜,他感觉好多了。他骑着电动车出了门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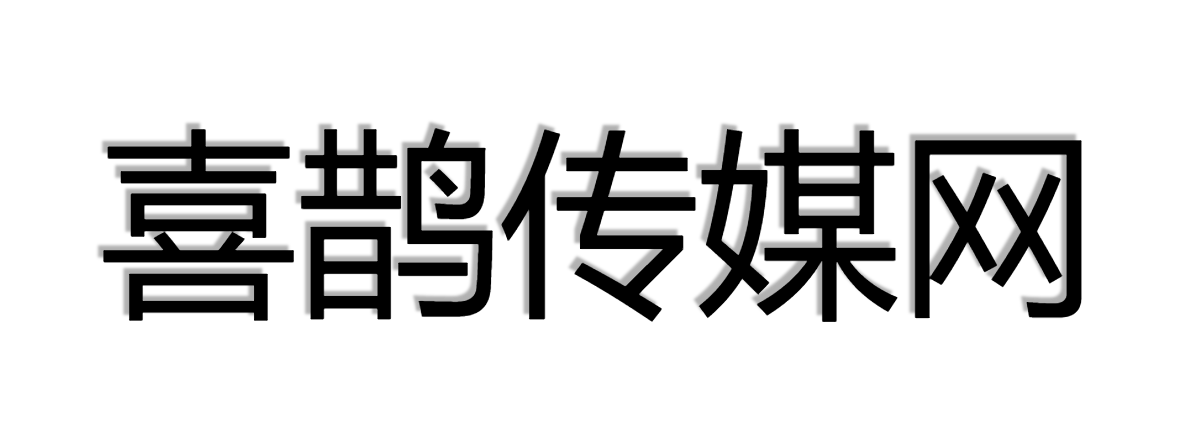

评论